近日,本报刊发独家探访“童工”家庭报道引起社会关注。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1月30日发出通知,将开展打击非法使用童工专项行动。
多名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表示,破解“童工”问题的关键在“疏”而不在“堵”。
“贫困是造成‘童工’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北京调查与数据中心主任赵卫华说。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今年5月在官网发布了《促进我省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总体上慢于全国人均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尤为突出。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3.7~4.59:1的高位,2012年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已达13947元。
贫困推动“童工”供给增加的同时,对“童工”的用工需求也真实存在。“利用‘童工’这类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在整个市场中获取基本的竞争优势,促进出口”——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楠在2012年作田野调查时发现,雇用童工多发生在箱包、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多集中于江浙地区。
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几乎看不到“童工”。李楠表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非常高,只有接受过教育或职业技术培训的人才能操控相关专业设备,“在这些行业里绝对不会出现童工”。
记者查询到,我国对禁止雇用童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一方面未成年工对工作的类型、强度等在心理上缺乏足够成熟的认知,另一方面未成年工在生理上还没有发育成熟,需要对其实行特别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国务院出台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列明了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
另外,1994年,当时的劳动部还专门颁布过《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具体规定了未成年工的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工作中需要长时间保持低头、弯腰、上举、下蹲等强迫体位和动作频率每分钟大于五十次的流水线作业”。
尽管有制度顶层设计,“童工”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邓锁认为,“童工”问题难以解决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缺位密不可分。在他看来,与城镇化相伴随的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对基础教育阶段农村儿童的发展有负面影响。“我国过去十几年实施的‘撤点并校’使大量的村校撤并,中心乡镇学校普遍推行集中住宿制,使得正式的学校教育较早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割裂,儿童的成长学习环境受到很大影响。”
邓锁曾在陕西农村调查发现,许多农村家长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并非持有“读书无用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家长外出打工赚钱是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但是,许多中小学生由于缺乏父母监督和与父母沟通,学习之外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容易出现厌学情绪或隐性辍学现象。
更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辍学到城市打工被一些地方默许,被当作一种自愿务工行为,不认为是一种对儿童权益的侵害,而没有得到更多干预和处罚,使得企业使用“童工”的违法成本降低,杜绝“童工”变成一句口号。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胡建国则认为,要加强劳动执法,不能只对雇用“童工”的小作坊采取惩罚措施,对业务转包的上游企业的失察,同样需要启动责任追究。
有专家认为,要真正解决“童工”问题,不仅要加强监管和立法两方面的力度,更重要的是,在“童工”产业链的两端发力——减少“童工”供给,降低“童工”用工需求。
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一些家庭来说,“童工”所挣的钱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所以与其呼吁反对血汗工厂、反对“童工”,不如思考如何给流入城市的“童工”提供更好的条件。
有专家认为,提供良好的条件、对口的职业教育,提升当地基础教育水平,实行点对点的精准扶贫和社会救助,多管齐下才能减少“童工”的产生。
“将外流的‘童工’遣散回原籍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贫困问题,而是需要考虑为其解决出路。”赵卫华说。
(责编:任婷(实习生)、熊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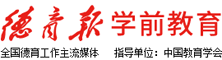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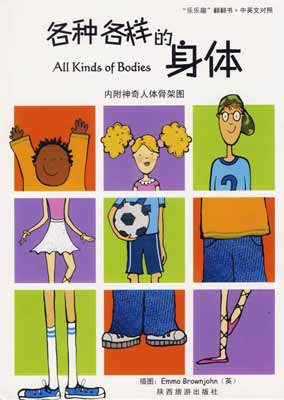



 有趣的根(大班科
有趣的根(大班科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 小班数学《求同求
小班数学《求同求 幼儿园托班教案《
幼儿园托班教案《 努力培养幼儿的语
努力培养幼儿的语 培养幼儿良好个性
培养幼儿良好个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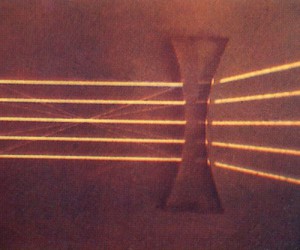 幼儿对光的朴素认
幼儿对光的朴素认 中班幼儿在新闻活
中班幼儿在新闻活 人工喂养宝宝不得
人工喂养宝宝不得 幼儿点菜权,轻松
幼儿点菜权,轻松 家常减肥食谱 瘦
家常减肥食谱 瘦 煲鸡汤,新妙招!
煲鸡汤,新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