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幼儿园
2010年的教育新政明显倾向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的盛宴或将终结
文 | 本刊记者 孙欣 编辑 | 王琦
2010年,是民办幼儿园最忐忑的一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其中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包括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同时扶持规范的民办幼儿园,对城乡民办幼儿园给予多种形式的扶持和资助。
既然扶持,既然资助,还忐忑什么呢?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规范民办园的“扶持”显得模棱两可,如何“资助”?给谁资助?不清晰、很复杂。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在发展公办园上的确很“大力”,例如北京市教委表示,在2015年前,北京将建设和改造600所幼儿园,政府办园比例达到50%,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80%建设为公办园,而这必然使得民办园的空间受到挤压。
事实上,中国60%的幼儿园都是民办园,尤其在二三线城市以及乡镇农村,经常一个县级市仅有三四家公办幼儿园。从90年代中期后,伊顿、汇佳、红黄蓝、艾毅、21世纪,一批小有名气的民办幼儿园横空出世,遍布京城。以硬件设施好、教育有特色、价格高著称。
一些被采访者表示,民办园的盛宴已经结束,接下来能够生存的是有品牌知名度的幼儿园,但利润空间将大不如前。
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一些风险投资也一度看中了教育产业的稳定性,投资民办幼儿园。淡马锡与艾毅、Hagerty与红黄蓝,都是那时结缘。他们给这些民办园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以期最终实现上市。
不过,眼下暧昧的政策导向,已经影响了民办园的发展进程,有的不得不推迟上市计划。一些新政策让民办园做的“很郁闷”。艾毅幼儿园总裁许尚杰说,以前房地产商建设好楼盘之后,对小区内建设何种幼儿园拥有推荐权,而现在教育部正通过发放建设幼儿园的指标,来逐渐收回自主权。这显然大大增加了民办园“拿项目”的难度。
公办园的增加,势必吸引民办园的幼儿教师向公办园流动,因为公办园幼教不仅工资较高,福利好,还有职称评定、退休金。如何招到并留住人才,成了民办园发展的又一大瓶颈。事实上,近一年多来,民办园的人员稳定性已明显下滑。
而在广大的三线城市及以下地区,民办幼儿园的生存处境将更加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受限于人们消费水平,很难“提价”,导致盈利水平较低。河北沧州金思维幼儿园曾试图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办高端园,但对方在仔细调研后,认为在沧州办高端园不赚钱,最终分道扬镳。
金思维的问题,正体现了三线城市学前教育的特性。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民办幼儿园的投资者往往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地方政府对民办园通常“只管不扶”,由于幼儿园属于“公益项目”,融资贷款也很难,导致其资金瓶颈凸显。“就像一个怪圈,资金少,收费低,老师工资就起不来,也就更留不住人。”金思维创始人杨宪章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幼儿园缺口最大的正是在这些地区。正规民办园的生存困境将无益于当地的早期教育。
眼下,巨大的生存压力已经让一部分民办幼儿园选择逃离。例如由新东方集团[6.99 1.60% 股吧]2006年创办的满天星幼儿园,如今已不再被总部看好,发展陷入停滞。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说,除了政策因素,新东方当初进幼儿园产业也有些盲目,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领导给予的支持也不够。
不过,仍有一批投资者孜孜不倦,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占有一席之地。“艾毅的目标是2011年建18家幼儿园,2012年建48家,”许尚杰乐观地说,“但我们只进一、二线城市。”
红黄蓝儿童教育公司董事长史燕来也表示对未来仍有信心。“大浪淘沙,未来能发展的只有那些有品牌的民办幼儿园。”有业内人士表示,红黄蓝“品牌输出”的模式有一定示范性。即做好品牌和研发,在一、二线城市以直营为主,三线及以下城市以加盟为主。
[案例1]
红黄蓝:“贵族”的压力
作为民办幼儿园的领先者,红黄蓝对发展模式、营商环境的摸索,其实有很多吃不准的地方
红黄蓝幼儿园方庄园,是高价园里的中档,但学费已经能让大多数平民老百姓感到囊中羞涩——普通班3000多元一个月,国际班5000多元一个月。工作人员表情愉悦地告诉记者,2011年的入学名额已经报满了。
红黄蓝如今在北京共有11家幼儿园,在外地一些城市,也设有分园。很多人说,它们简直是吸金机器。但听了这话,红黄蓝儿童教育公司董事长史燕来只是一丝苦笑。
2010年,国家的新政策给了民办幼儿园投资者们沉重的一击。由于国家决心大力推动公办园的发展,民办园建园难的问题日趋明显。每次红黄蓝参与竞标时,总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公办园,中标难度加大,审批环节也更复杂。“假设我们预计每年开20个幼儿园,现在最多只能开一半。”至于上市时间已经一再推迟,“过两年再看吧。”她的话里多少有些无奈。
其实,红黄蓝从2003年开办第一家幼儿园至今,它的发展速度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快。前四年,平均每年只开一家园。到2008、2009两年,已经引入两轮投资,财力雄厚的红黄蓝还出人意料地将刚推行不久的加盟业务暂停了8个月。做的时间越长,史燕来就认识得越清楚。“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赚钱,幼儿园肯定做不好。”
1998年,史燕来进入了儿童早教(红黄蓝称其为亲子园)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并将红黄蓝做成了行业领先的早教品牌。“如果红黄蓝专心做亲子园会不会更好?”这个疑问,不仅同行有,连史燕来的创业伙伴也拿不准。
据说,当时为了做不做幼儿园,创业团队争论得很厉害。因为那意味着将前几年赚的利润都投进去,还不够,而且与亲子园相比,办幼儿园的利润低,投资大,回收期长。
但史燕来很坚持。她希望实现0-6岁的儿童教育的一体化,在她的规划里,将来幼儿园不仅能挣钱,还能与早教相互配合,达到协同作用。她算了笔账,投资一家亲子园大概需要50万—80万,净利润达30%多,回收期快的不到一年。而幼儿园投资是亲子园的10倍左右,大概为300万至600万之间,回报期大约两年,但一旦稳定后,经营难度比亲子园低,回报稳定。她最终说服了其他人。还鼓动30多位股东共同入资,筹得180万元。
现实比他们预想的要好。由于北京消费者对幼儿园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不到一年半,第一家红黄蓝幼儿园右安门园就收回了成本。
或许你就此以为,办幼儿园很简单,但事实绝非如此。在消费市场日趋成熟的一线城市,如果民办园做不出特色和品牌,则很难真正成功。因此,初战告捷的红黄蓝幼儿园并未放开四蹄,一路狂奔,史燕来选择了一条谨慎的道路,“必须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跑得更远。”
从2003年到2005年,红黄蓝一直在两个方向上下苦功。一是科研,红黄蓝的科研中心和一线园长、主任、老师组成团队,一起研究办学特色。二是努力获得教育部门的认可。史燕来提出每一个红黄蓝幼儿园必须达到一级一类园。“在国内做教育,如果不被教委认可,很难做大。”
记者参观了整个红黄蓝方庄幼儿园,其用心程度可圈可点:每层楼有不同的主题。在楼外的活动场地,还有养着鹅和兔子的小型动物园、种植角、三叉山洞等。
除了在硬件上的投资,红黄蓝还在课程设计上和公立园有所区别——以通用教材为主,兼有补充性的特色教程,经过研发将课程设计为6大项—身体运动发展、数学发展、艺术与创造力发展(纸工坊、泥工坊等)、个性社会性与情感发展、沟通表达发展以及认识和理解世界。
“民办园和公立园相比,最显著的优势还是对每个学生的重视和呵护。”史燕来要求幼儿园老师对孩子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并对幼儿园的卫生提出高要求,例如园内的沙池在闭园后必须盖上沙池布,防止猫狗跑进去,第二天7点才能打开。
红黄蓝还定期组织孩子们外出活动,写生、采摘或是去养老院慰问。而这在许多幼儿园,甚至是一些公办园,都不愿意做的事,因为这不仅耗费精力,还承担风险。
2008年9月,美国艾威基金投资红黄蓝,华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在投资者的帮助下,红黄蓝重新梳理了商业模式,确定了红黄蓝亲子园和红黄蓝幼儿园互动连锁发展的模式。他们发现,红黄蓝亲子园和幼儿园理念互通,课程也都是围绕6大领域做,品牌的空间利用率也有很多整合。例如幼儿园在周末开亲子班,亲子班平时做幼儿园的过渡课程。另外,在全国布局、管理系统上,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但在是否发展加盟的问题上,投资者曾一度和史燕来发生分歧。投资者认为红黄蓝幼儿园不应该做加盟,而史燕来则认为,各地存在特殊性,红黄蓝无法直接到达,必须依靠当地加盟商才能办园。2008年,红黄蓝突然决定停止加盟业务长达8个月。而红黄蓝也借这8个月详细梳理了有关加盟的许多问题。大家意见一致后,红黄蓝的加盟业务才又继续推行。
2010年,国家一道有关幼儿园的中长期政策又给红黄蓝的发展平添了变数。“现在很多地方建幼儿园,第一考虑公办,第二才考虑民办。”史燕来说,而随着公办园的增加,民办园的“高价”也受到挑战。
“但民办园只有高价才能生存。因为它的成本比公办园高很多。”史燕来说。另一方面,民办园老师的稳定性已经一再下降。公办园可以提供稳定的薪酬、福利,以及职称评定。“我们靠设计更吸引人的薪酬体系、晋升通道甚至股权激励来留住老师,同时带领团队形成学习的气氛,用科研留人、发展留人。另外,我们也不断寻求政府的支持。”
最近,北京丰台区召开今年最大规模的教育工作会议,红黄蓝作为唯一的民办园代表参加了会议。“各区县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也开始关注优秀的民办幼儿园品牌,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史燕来说,她相信,未来生存不是问题。当然,他们也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努力获得政府的认可。
[案例2]
金思维三线园的压力
“现在大多数老师还是想去公办园。”公办园的老师不仅工资不低,还有职称评定,而且工作也相对稳定
在别人眼里,杨宪章这几年肯定是发大财了。金思维成了沧州最有名望的民办幼儿园。尤其位于市中心的老园,虽然价格在沧州属于中高端,但依旧生源爆满,很多家长需得找关系、批条子才能挤进来。由于做得好,杨宪章去年又在沧州投资了两所新园。
可谁能想到,背着人时,杨宪章就像另一个人。他会突然嚎啕大哭,会歇斯底里地大叫,会砸碎家里的各种东西,甚至把花盆里的土一股脑倒在床上。有时候,连他老婆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心理压力太大了,有时又不便向别人倾诉。”杨宪章说,做了民办幼儿园才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尤其在三线城市,更是“受气不挣钱”。他很羡慕一线城市的民办幼儿园,“创业环境好,有钱人多。”
河北沧州,中国一个普通的县级市,有680万人口,可公立幼儿园仅有4家。长期以来,鱼龙混杂的私立园“承包”了这里的学前教育。
“我总结了两句话,在一线城市越规范、做的时间越长越赚钱,能做到资本的增值;三线城市越不规范、做的时间越短越挣钱,规范的只能做到资产保值。”杨宪章喝了口酒,大声地说。席上,金思维的园长们都不做声,有人叹了口气。
在杨宪章的所见所闻里,沧州有两种幼儿园容易赚大钱。一是不规范的幼儿园,二是干了不到5年就转卖的幼儿园,因为这样避免了二次改造。“有一个人,干了4年幼儿园不干了,卖了800万。”杨宪章的话语间带着复杂的情绪。
很遗憾,杨宪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他对教育工作有种偏执的爱好,为此,他放弃了学校团支部书记的工作,甚至背着前妻卖了自家房子,又委托朋友担保贷款,才筹集了20多万元,在2003年建立了金思维幼儿园。但现实并未对他的热情格外照顾,他自嘲自己如今越来越像一个“教育志愿者”。
怕我们不信,杨宪章算了笔账。
按照他崇尚的国学思维,每个金思维幼儿园都设有两个园长,分别管后勤和业务。此外,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后勤部、保安、班车司机等一应俱全。每年人员开销就达二十几万。而规模最大的一家金思维幼儿园约有400个孩子,每人每月学费约600元,扣掉不出勤的退费,每年收入150多万。扣除成本后,每年一所园的利润大约五六十万。几年下来辛苦攒点钱,杨宪章又全投到了两所新幼儿园的建设上。“我现在烦恼的是,大家都觉得我很有钱,其实我根本没挣到多少钱。”
主要问题就出在价格上。杨宪章又搬出一笔账:沧州一个幼儿园老师的月工资大约2000元,而北京幼儿园老师的工资也在2000左右。但同等质量的幼儿园,沧州每月学费只有500元-700元左右,而北京则要两三千元甚至更高。如此一来,北京平均0.67个孩子养一个老师,而在沧州则要2.78个孩子养一个老师;北京平均每月只需要22个孩子的学费就能抵消房租费,但沧州需要32个孩子;北京47个孩子的学费就能抵消幼儿园所有员工的工资,而沧州需要138个孩子。显然,在北京办幼儿园的利润率远高于沧州。
“一线城市有钱人太多,幼儿园的功能已经发生异化,不仅仅是幼儿教育,还承担着消费功能。因此,建的越好,价格越高,越不愁生源。而在三线城市,就恰恰相反,有钱人就那么多。”杨宪章苦笑道。
据说杨宪章原本找了一家公司合作,希望自己买地,在沧州建一所高端幼儿园。但合作方经过考察,认为在沧州建高端园不赚钱,最终分道扬镳。
不如意的经济账并不会让杨宪章陷入那种歇斯底里的愤怒。让他真正恼火的,是赚钱不多却受气。他有些不好意思提到他的发泄,“让我痛苦的事很多,我已经不记得具体哪一件了。”他力图回避,但又渴望倾诉。
终究,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归结起来,压力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找钱难,二是和政府部门关系的处理,三是与社会上某些人群的纠纷,四是幼儿园经营上出现的种种问题。
资金问题,是杨宪章这种财力薄弱,又希望扩大经营规模的幼儿园投资者的最大困扰。最初建园就几乎花掉了杨宪章所有筹来的资金,直到3年后,金思维幼儿园才基本收回成本,而杨宪章的第一任妻子也由于难以忍受而提出离婚。
此后由于幼儿园属于公益性项目,贷款时不能作为抵押物,资金掣肘一直影响着金思维的发展。他连2010年在沧州建两所新幼儿园都捉襟见肘。由于四处找钱不得,杨宪章只能求助于家长,每人借款4万元,最终筹得借款200万元,而这50个孩子三年的学费餐费全免。
除了资金,还有很多难言的苦闷。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各基层部门人员吃饭、处关系。”杨宪章说,幼儿园的特殊性,导致它涉及的监管部门繁多,卫生、食品、消防、教育……无一不在挑战金思维的公关能力。
更麻烦的,还有同行的威逼挑衅。有时,杨宪章不得不做出妥协,答应威胁者的条件。“我不是没办法,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它违规了,以后一定会有恶果。”其余,便更多是幼儿园的内部问题。“我是老板,哪怕出了点小事,许多家长都会直接找我。而我无人可找,必须解决。”
如今,杨宪章的难题更多了。根据2010年中央关于幼儿园的新政策,仅沧州运河区一个区就要在未来3年新建20所公办幼儿园。金思维将面临更多公办园赤裸裸的不公平竞争。
“眼下最难的问题是如何留住有经验的幼儿教师。“一位园长插话,“现在大多数老师还是想去公办园。”公办园的老师不仅工资较高,还有职称评定,而且工作也相对稳定。
而一些公办园也开始施展招数,抢夺生源。例如与小学利益挂钩,招收学前班,吸引金思维等民办幼儿园的大班生源。在这些方面,杨宪章深感“以卵击石”。
更严峻的是,如果政府执行“国办民办同价”,那么,杨宪章的处境将更糟。一旦民办园的价格上不去,老师的工资就上不去,人员稳定性必然下降。
“民办幼儿园是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我最高兴的,是有家长在孩子毕业之后还来感谢我,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价值。”杨宪章说完,指了指幼儿园旁边一个80年代的老楼房。他和女儿就租住在这里,默默守着他的幼儿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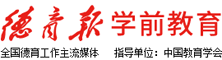










 学习活动——鸟是
学习活动——鸟是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 半日活动详案
半日活动详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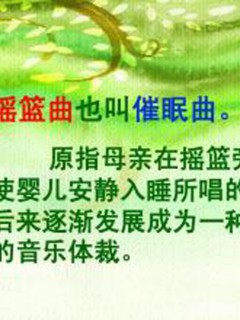 托班教案:摇篮曲
托班教案:摇篮曲 浅谈幼儿“早期识
浅谈幼儿“早期识 培养幼儿良好个性
培养幼儿良好个性 “动”起来,让科
“动”起来,让科 浅谈幼儿交往能力
浅谈幼儿交往能力 20套适合孩子的营
20套适合孩子的营 爱它吧 春天就是
爱它吧 春天就是 小儿积食厌食怎么
小儿积食厌食怎么 重庆风味辣子肥肠
重庆风味辣子肥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