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研究以347名回、藏、汉族3~6岁幼儿家长为调查对象,对幼儿语言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回、藏、汉族3~6儿童语言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汉族儿童发展最好;藏族儿童在日常用语的理解方面显著高于回族儿童;在交流和转述方面,汉族儿童非常显著地高于回族儿童;在交流、转述和对时间的理解上,汉族儿童显著高于藏族儿童;不同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及母亲的教养对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3~6岁幼儿;语言发展;回族儿童;汉族儿童;藏族儿童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藏族和回族作为我国西部特有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多,并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其中,回族信仰伊斯兰教,长期和汉族杂居,一直和汉族共享汉文字。藏族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独立的文字和语言。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交流对各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其成长,尤其是语言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强调认知结构及儿童与成人的语言交往对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作用。[1][2][3]在儿童语言获得过程中,其年龄、性别、所处文化背景、母亲的教养等都会对其语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拟选取回族、藏族和汉族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以期发现不同民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为有效促进不同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儿童语言发展提供建议。
二、 研究方法
被试取自回族、藏族和汉族,共347名幼儿家长参与问卷调查。所有幼儿的年龄分布在3~6岁,其中3~4岁116人,4~5岁108人,5~6岁123人,回族126份,藏族126份,汉族95份。男性幼儿178名,女性幼儿169名。
本研究采用日本早稻田大学人类科学部心理学教授清柳肇和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周爱保教授合编的幼儿发展问卷(家长用),使用语言表达和理解以及母亲平时表现三个分测验,首先对这些分测验进行项目分析,删除无显著相关的题项,然后进行信度检验,幼儿语言表达问卷共17题,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006;幼儿语言理解问卷共20题,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95;母亲平时情况调查问卷共20题,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777。接着分别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样本充足性检验,语言表达问卷的球形检验值为2323.959,P<0.001,KMO值为0.883;理解问卷的球形检验值为1529.851,P<0.001,KMO值为0.785;母亲平时表现问卷的球形检验值为746.356,P<0.001,KMO值为0.792。这说明三个测量检验项目间可能有共享因子,适合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因素分析。问卷由幼儿家长填写。对收集的数据利用SPSSl0.0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对幼儿语言发展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析出四个因子,分别是有情景的交流、转述,对时间的理解和对日常用语的理解。对民族、幼儿性别、幼儿年龄和母亲是否有工作的Pillai’s整体检验结果显示:幼儿性别和母亲是否有工作的主效应不显著,F(1,228)=1.961,P>0.05,F(1,228)=0.744,P>0.05;民族和年龄的主效应均显著,F(2,228)=4.012,P<0.001,F(2,228)=3.507,P<0.001;性别和民族、性别和年龄之间交互作用显著,P<0.05;民族和年龄、性别之间交互作用非常显著,P<0.001。组间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性别在幼儿语言转述因子上差异显著,P<0.05;民族在语言发展四个因子上差异均显著,P<0.05;年龄在转述这一因子上临界显著,P=0.059,在交流和对时间的理解方面差异显著,P<0.05。
表1 民族、性别和年龄在语言发展各因素上的平均数摘要
|
因素 |
有情景的交流 |
转述 |
对时间的理解 |
对日常用语的理解 |
|
民族 |
回族 |
51.8144 |
18.7736 |
20.6786 |
20.9022 |
|
藏族 |
52.0952 |
18.9060 |
20.1395 |
22.0795 |
|
汉族 |
55.2391 |
21.4043 |
23.3511 |
22.6383 |
|
性别 |
男 |
53.8105 |
20.0552 |
21.2647 |
21.9231 |
|
女 |
52.0214 |
19.0844 |
21.6172 |
21.8244 |
|
年龄 |
3~4岁 |
43.8387 |
17.2857 |
17.3333 |
21.0323 |
|
4~5岁 |
51.2907 |
18.6771 |
19.2785 |
21.7529 |
|
5~6岁 |
54.4727 |
19.9304 |
22.5941 |
22.0792 |
表2 民族和年龄在语言发展各因素上的事后比较(LSD)
|
因素 |
有情景的交流 |
转述 |
对时间的理解 |
对日常用语的理解 |
|
民族 |
回族—藏族 |
.420 |
.546 |
.478 |
.006 |
|
回族—汉族 |
.003 |
.002 |
.000 |
.000 |
|
藏族—汉族 |
.028 |
.011 |
.004 |
.371 |
|
年龄 |
3~4—4~5 |
.082 |
.051 |
.092 |
.429 |
|
4~5—5~6 |
.001 |
.260 |
.000 |
.138 |
|
3~4—5~6 |
.024 |
.185 |
.000 |
.323 |
注:表格内显示的数据为两两比较的显著性水平
表1和表2结果显示:女童的语言转述能力高于男童,P<0.05。藏族儿童在日常用语的理解方面显著高于回族儿童,P<0.05,在其他三个因子上回藏儿童差异不显著;在语言表达因子上,汉族儿童显著高于回族儿童,P<0.05;在语言理解因子上,汉族儿童非常显著地高于回族儿童,P<0.001;在有情境的交流、,转述和对时间的理解三个因子上,汉族儿童显著高于藏族儿童,P<0.05。在年龄变量方面,3~4岁儿童与4~5岁儿童在转述能力上的差异临界显著,P=0.051。3~4儿童的转述能力稍低于4~5儿童。在有情境的交流中,5~6岁幼儿均显著高于3~4岁和4~5岁幼儿,P<0.05。对时间的理解方面,5~6岁幼儿非常显著地高于4~5岁和3~4岁幼儿,P<0.001。在其他因子上,年龄变量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对母亲基本表现的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析出四个共同因子,分别是出世的态度、育儿知识、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对待丈夫的态度。对民族和母亲是否有工作的Pillai’s整体检验结果显示:民族和母亲是否工作的主效应均显著,F(2,228)=2.215,P<0.05,F(1,228)=3.022,P<0.05;组间检验结果显示:民族在母亲对丈夫的态度方面差异显著,P<0.05;母亲是否有工作在育儿知识方面差异临界显著,P=0.057,在对孩子的态度和对丈夫的态度方面差异均显著,P<0.05。表3的结果显示,没有工作的母亲比有工作的母亲更缺乏育儿知识,对待孩子的态度更为冷漠,而对丈夫更尊敬和依赖。民族和母亲是否工作在母亲基本表现四个因子上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变量在母亲表现的第四个。因子上的差异非常显著,P<0.001,其中回族的母亲最依赖丈夫,达到显著性水平,其次为藏族母亲,汉族母亲更独立一些,但藏汉两族之间未达到显著水平(见表3、表4)。
表3 民族和母亲是否工作在母亲表现四因子上的平均数摘要
|
|
处世态度 |
育儿知识 |
对待孩子的态度 |
对待丈夫的态度 |
|
民族 |
回族 |
8.6972 |
5.6814 |
5.8929 |
6.1083 |
|
藏族 |
8.2477 |
5.8929 |
5.2696 |
5.3500 |
|
汉族 |
8.6477 |
5.3182 |
5.5165 |
4.9000 |
|
母亲是否工作 |
是 |
8.4363 |
5.5048 |
5.2897 |
5.1644 |
|
否 |
8.7071 |
5.9800 |
6.1683 |
6.1667 |
表4 民族变量在四个因子上的事后比较(采用Scheffe法)
|
|
处世态度 |
育儿知识 |
对待孩子的态度 |
对待丈夫的态度 |
|
回族—藏族 |
.200 |
.930 |
.133 |
.003 |
|
回族—汉族 |
.697 |
.100 |
.331 |
.000 |
|
藏族—汉族 |
.398 |
.100 |
.637 |
.235 |
注:表格内显示的数据为三个民族之间两两比较的显著性水平
以幼儿语言发展的四个因子分别为因变量,以母亲表现的四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母亲表现的四个因子中,母亲的育儿知识、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对待丈夫的态度对预测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三个自变量分别联合解释了25%、5.3%、16.1%和15.1%的儿童语言发展差异(见表5)。
表5 母亲表现各因子对儿童语言发展各因子回归分析决定系数
|
|
有情景的交流 |
转述 |
对时间的理解 |
对日常用语的理解 |
|
变量 |
R² |
R² |
R² |
R² |
|
处世态度 |
.000 |
.000 |
.001 |
.001 |
|
育儿知识 |
.079 |
.014 |
.051 |
.047 |
|
对孩子的态度 |
.081 |
.015 |
.055 |
.049 |
|
对丈夫的态度 |
.090 |
.024 |
.055 |
.055 |
四、讨论
(一)回藏汉三个民族幼儿语言发展的相同之处及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三个民族不同性别的幼儿在语言发展方面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对于幼儿转述能力的发展方面,女童的发展明显高于男童。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女孩语言发展优于男童的日常经验。其次,母亲是否工作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是潜在的,主要通过影响母亲平时的教养态度或教育方式对幼儿语言发展产生影响。没有工作的母亲相对来说文化素质较低,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更少可能从他人或书本获得育儿的科学知识,不懂得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在人格上也更依赖丈夫。不过,孩子3岁以后,大多都进入幼儿园,由于这些保教机构有正规而系统的语言训练,母亲对孩子语言发展的直接影响会相应减小。第三,在年龄变量方面,幼儿年龄越大,语言发展水平越高,特别是交流能力和对时间的理解能力。这可能主要因为4~5岁的幼儿均已进入书面语言发展的敏感期,这个概念不单纯是个年龄概念,同时是个经验概念,个体需要有一定书面语言的经验才会进入这个敏感期。[4]
(二)回藏汉三个民族幼儿语言发展的差异及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回藏汉三个民族的儿童在语言发展方面各有优势,但总体上汉族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藏族。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可能与回藏两个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藏族人民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绝大多数的家庭曾经或一直使用藏语言,只有孩子进入托幼机构后才开始接触汉语言。因此,对藏族儿童来说汉语言属于第二语言,需要依靠藏语来理解汉语。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其回语言属于阿语语系,虽然回族家庭使用阿语的频率不及藏族家庭,但浓厚的宗教文化使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民族宗教文化的熏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非常高的认同,并且这种宗教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成为回族儿童学习汉语言的重大障碍。这种特殊的文化与民族背景必然使藏、回儿童在以汉语为主流文化语言的问卷调查中显示出弱势。可见,语言不仅是符号系统,而且“是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即它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5]
第二,和汉族相比,藏、回族聚居区大都处在深山大川之间,交通不便,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托幼机构设施单一,双语师资欠缺,从而大大延缓了这两个少数民族儿童语言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社区学生学业成绩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为社区不同,提供给孩子的各种资本是不同的,就教育社会资本而言,不同社区对双语儿童的教育期望存在着差别,这种教育期望就相当于一种社会资本,不同社区孩子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别即是这种社会资本差别的一种反映”。[6]
第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幼儿语言的获得依赖于一定的认知发展水平。只有当儿童能区分语词所指示的事物时,才能真正掌握。约翰·麦克纳马拉研究发现,儿童学习语言,开始时不是依赖语言,而是先确定对方想对自己表达的意义,进而弄清意义与自己所听到的叙述之间的关系。[7]按照皮亚杰的理论,3~6岁幼儿思维处于前运算阶段,并以自我中心为典型特征,通常用已有的认知结构同化客观世界,而不是采用顺应的机制接受外界的新刺激。[8]由于长期以牧业和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落后等原因,藏族和回族儿童相对入学较晚,汉语言经验积累较少,同时受到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在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言时必然面临比汉族儿童更大的困难。
第三,在家庭教养方面,母亲是幼儿的第一重要他人,其教育方式对幼儿的认知发展、性格形成、自我概念、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9]已有研究发现,母亲的教养敏感性与婴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呈正相关;在早期交流技能上得高分的婴儿可由较积极的母亲和儿童的气质所辨认,儿童和母亲的相互作用变量在学前期比在婴儿期能解释更多的儿童心理变化。[10][11]这些结论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没有工作的母亲在母亲表现四个因子上的表现均低于有工作的母亲,也就是说没有工作的母亲更消极、更缺乏育儿知识、不懂得很好地处理亲子关系,也更依赖丈夫。回族没有工作的母亲高达59%,藏族只有1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族和藏族家庭教育的差异。而且,回族家庭教育中还有一种独特的家庭教育模式——经堂教育。经堂教育一般分“小学”“中学”“大学”三部。“小学部”对回族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回族儿童一般在四岁零四个月就要“迎学”,被父母送至清真寺或阿訇家中接受教育。阿訇从阿拉伯字母和阿语拼读教起,为儿童以后熟练地诵读《古兰经》打下基础。在此阶段,阿訇还要求儿童熟练地背诵《亥听》(《古兰经》文选),背诵和学习《杂学》(伊斯兰教基本常识),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生活习惯。一般来说,儿童能独立正确诵读《古兰经》,“小学”即可毕业。叫经堂教育对回族的生存发展及回族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对其他文化与宗教的绝对排斥态度对回族儿童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汉语言则会产生极其不利的消极影响。
五、结论
第一,回、藏、汉族3~6儿童语言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汉族儿童发展最好。
第二,藏族儿童在日常用语的理解方面显著高于回族儿童;在交流和转述方面,汉族儿童非常显著地高于回族儿童;在交流、转述和对时间的理解三方面,汉族儿童显著高于藏族儿童。
第三,不同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1]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180
[2]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7:98
[3]刘华.论幼儿母语教育.学前教育研究,2005,(1)
[4]莫雷等励儿书面语言掌握特点的实验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5,(7)
[5](俄)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贵孝通译.北京:中 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7
[6]邢强.影响藏族双语儿童学习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1,(4)
[7]刘电芝,洪显利.影响儿童早.期语言获得的主要因素,学前教育研究,2000,(6)
[8]陶明远。藏族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与教育.民族教育研究,1994,(3)
[9]林磊等.母亲教养方式与学龄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6,(4)
[10]Regina M.Cusson.Faetors influencing preterm infant language development.Jobstet Gynecol Neonatal Nuts,2003,32(3):402-409
[11]Fish M,Pinkerman B.Language skills in low—SES rural Appalachian children: norm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infancy to presch001.Journal OfApplied Development Psychology,2003,23(4):539—565
[12]海存福.回族家庭教育的发展回族研究,2000,(4)
作者单位:
夏瑞雪 甘肃联合大学经管学院
周爱保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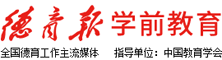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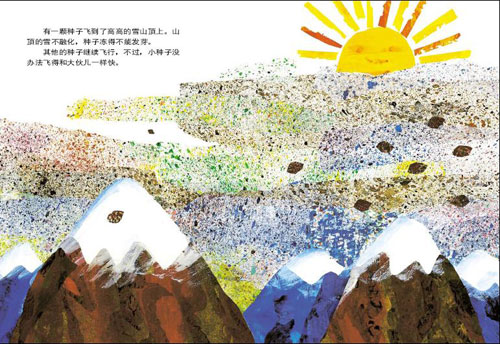



 大班语言活动设计
大班语言活动设计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 小班数学活动:图
小班数学活动:图 主题活动《拇指贝
主题活动《拇指贝 浅议幼儿语言教育
浅议幼儿语言教育 共建心理健康通道
共建心理健康通道 注重孩子的探索与
注重孩子的探索与 浅谈幼儿责任心的
浅谈幼儿责任心的 妈妈给宝宝喂奶该
妈妈给宝宝喂奶该 你丢掉的菜根都是
你丢掉的菜根都是 家常减肥食谱 瘦
家常减肥食谱 瘦 一周七日最佳早餐
一周七日最佳早餐










